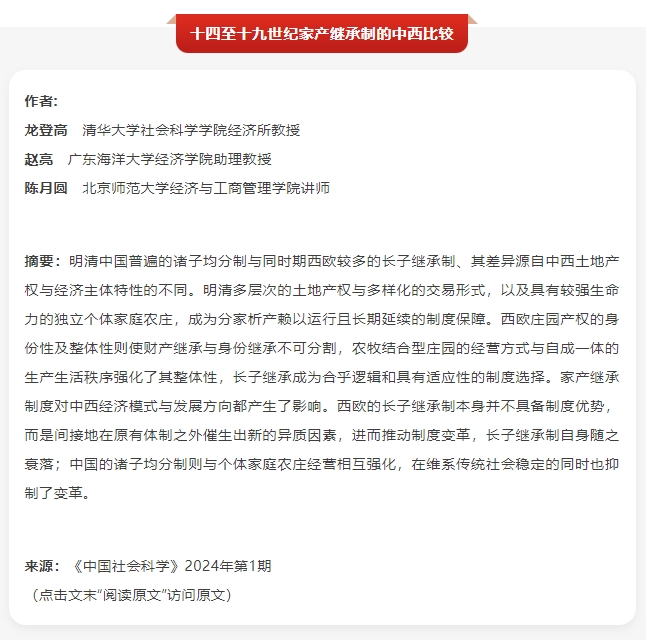
近日,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龙登高课题组从产权制度与基本经济主体入手进行比较研究,揭示14-19世纪中西家产继承制度的共性、差异及其经济逻辑。
诸子均分制在传统中国长期广泛流行,在中世纪与近代西欧则居于次要地位。长子继承制在中世纪与近代西欧较为突出,并被不少学者视为近代西欧率先实现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优势,但这是一种误读。以往归咎于文化差异,这失之宽泛,甚至适得其反。本文从产权制度与基本经济主体入手进行比较研究,寻找14-19世纪中西家产继承制度的共性、差异及其经济逻辑,希冀形成系统性的认识框架。
长子继承制在西欧较为突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庄园制度之下家产继承与身份继承不可分割,身份性产权之下无论庄园主还是农民,分家析产都不可行。二是庄园经营的整体性。农牧结合型庄园从休耕、轮作与敞田制,到公地的共同使用,还是大型生产设备与工具,及各生产环节和产业链的生产协作,都使得庄园自成一体。庄园作为基本经济单位,难以分割与交易,长子继承能够适应、维护庄园的整体性,因而具有可持续性。
明清中国则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多层次土地产权及多样化交易形式,有助于农户田地析分与动态配置,分家书以契约的形式表达了明确的产权归属,成为一种产权凭证与交易凭证,具有法律效力。个体农户依托要素市场与商品市场,借助各类民间组织实现基层秩序与公共品供给及风险分担,从而实现低门槛的独立经营,具有较强韧性和生命力。因此尽管诸子均分制使个体家庭耕种土地的规模逐渐减小,家庭再生产仍能有效维系,较之世代同堂大家庭与规模化农场具有适应性与竞争力。
中西继承制度的差异深刻影响了各自经济演进与制度变迁的路径。在西欧长子继承制地区,分流出的“小儿子们”在原有体制与领域之外谋生、发展,新的异质因素逐渐成长,进而不断冲击原有的本质因素,最终形成挑战、改变旧体制的力量。西欧的近代变革不是长子继承制本身所带来的,恰恰相反,在现代产权制度的革命性变化完成后,长子继承制走向终结,身份性、特许性权利逐渐拓展为普惠性的权利,子女平等的现代继承制取而代之。也正是在这一历史性的变革之中,人们对于基督教教义的理解发生转变,从长子继承神圣性的天主教伦理逐渐让位于强调平等的新教伦理。长子继承与现代继承制的取向大相径庭,但本文避免以“落后”称之,而是挖掘其符合特定时期的经济逻辑及历史合理性。
相应地,明清中国的诸子均分制与低门槛、可复制、易恢复的个体家庭农庄相互强化,使得传统经济具有活力与韧性,长期处于稳定状态,冲击传统体制的变革因素未能成长。或者说,传统中国诸子均分制下个体小农经营相对稳定,变革的异质因素消融于原有体制之中,但也使得总体性的变化难以发生,唯其稳定,难以变化。
本文从家产继承制度的经济逻辑出发,系统解释继承制度与经济演进的互动关系,在消除种种成见与误解的同时,为理解中西经济的基本特征与“大分流”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理论解释。
相关成果以“十四至十九世纪家产继承制的中西比较”为题,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龙登高为论文第一作者。论文发表后先后获得《新华文摘》(2024年第8期“论点摘编”)、《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4年第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2024年第3期)、《社会科学文摘》(2024年第6期)转载。
